在芸芸众生的大上海,他是一名“淘金者”。他所从事的行当是在浦东开发区拆房。当年,他仅仅是拆房大军中的一名民工,从民工到包工头,再由包工头到当上陆家嘴市政绿化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项目经理,这便是他十多年“淘金生涯”的奋斗里程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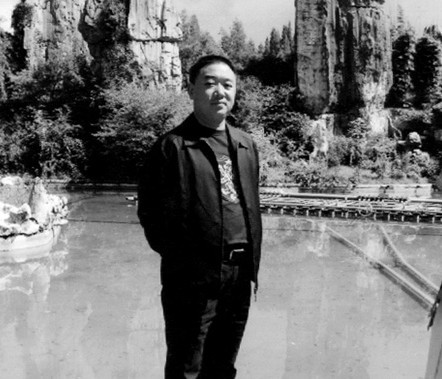
星夜离家,他留下一张特别借条:“乡亲们,欠你们的钱我会连本带息偿还的!”
黄善云出生在云阳县后叶乡。1984年高中毕业在家开起了粉房。后叶乡地处云阳县大山深处,山民们难以找致富的出路,在他的带动下,山民们纷纷开始开发丰富的洋芋、红苕资源,生产洋芋粉、红苕粉供应城里的批发市场和火锅店。在山民眼里,黄善云是个有文化、见识广、肯帮忙的好后生,许多山民生产的粉条都放心地交给他拿到城里去批发。
1985年9月,他走村串户把山民们的粉条收罗起来,共28吨,足足装了两卡车。这两卡车粉条是万州干果公司向山民们定购的产品,同时也提出了严格的质量要求。后叶乡的山民们也为找到了一个大买主而由衷地高兴。
那天,黄善云随车押运粉条到万州交货,刚刚上路,天阴沉下来,黄善云不时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察看老天爷的脸色,担心货没运拢就下起雨来。这两车粉条,山民们早已盘算好了如何开销,等着黄善云把钱拿回去解决孩子的学费以及购买农用物资等等。如果被雨淋湿了,万州干果公司必然拒收,并且好不容易找到的一家大买主从此不会再往来。
老天不长眼,雨真的稀里哗啦下了起来。路上,卡车找不到避雨的地方,粉条被淋湿了,黄善云在车里急得捶胸顿足,无奈之下,他还是把两车粉条运到了万州干果公司。万州干果公司的经理和业务员们望着两车被淋湿的粉条皱起了眉头。第二天,部分粉条生了霉,在黄善云的再三恳求之下,万州干果公司还是收下了这批货,但每斤收购价仅0.4元。两车粉条一下亏了1万多元。1万多元的亏损,对刚开始做生意的黄善云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,他感到无法回去向父老乡亲们交代。他怀揣结算的两万多元货款在车站徘徊了很久,但还是鼓起勇气登上了回家的客车。
回到家,结算粉条钱的乡亲们来了,他把亏损的情况向乡亲们诉说,希望得到理解,但满怀希望的乡亲们却炸开了锅:“我们交的上等粉条,凭什么只卖0.4元一斤?”“运货时就应该防雨,这不该我们承担责任。”
有的乡亲甚至怀疑黄善云贪了大家的钱。无奈之下,他结算了部分货款,打发走了吵闹的乡亲,余下的1万多元远远不够第二天上午的结算。他想了很久很久,萌发了外出打工挣钱偿还乡亲们的想法。深夜两点,他向熟睡的老母亲床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躬,然后提笔写了一张欠条:“乡亲们,我对不起大家,我把尚未结算的1万多元带走了,这是你们借给我的钱,作为外出打工的盘缠,请你们相信,我欠你们的钱会连本带利还给你们的”。
写完欠条,他轻轻地拉上了大门,徒步走出大山,乘上去陕西西安的长途客车。
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当地人看不起的职业。可10多年过去了,上海人却称赞重庆民工为浦东开发功不可没。
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黄善云来到西安举目无亲,四处谋职,四处碰壁。好在身上还揣着1万多元现金,就靠这1万多元现金过起了漂泊的日子。1987年春节刚过,他听说走在改革开放前面的上海发财机会较多,毅然登上了南下的列车。到达武汉,再从武汉乘船赶到上海。他在“十六铺”码头下了船,对岸就是刚刚起步开发的浦东开发区。
他来到一个拆房工地的工棚面见拆房老板,老板疑惑地看着这个衣着干净整洁的小伙子说:“在我们这里当小工,每天只有5元钱,非常苦、非常累,甚至还有生命危险……”
黄善云告诉他:“再苦没有无所事事苦,再累也没有背着沉重的债务包袱无法偿还的那种心累。”第二天,他就和工友一起爬上楼房墙体,抡起大铁锤“砰砰砰砰”地干起来。一天下来,从头到脚都是灰尘,全身累得骨头要散架,可他从不叫苦叫累。
老板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:这是一个好后生。有文化,能吃苦,今后是个好帮手。
两个月后,老板就提拔他当管理员,管理民工队伍和施工现场。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:“小黄啊!浦东是个大工地,这里的上万民工大都来自长江三峡,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上海人看不起的工作,许多上海人瞧不起我们这些民工,甚至把我们称为盲流。这个行业很有钱赚,我们一定要在这个行业干出成绩,混出个人样来,让上海人看到我们三峡人吃苦耐劳、聪明能干的精神。”
老板的话如雷贯耳。黄善云暗记心间。
来到上海的几年间,他没向家里写过信,也没和家乡通一次电话。在乡亲们心目中,黄善云消失了。1992年,已经积累了一些资金的黄善云挂靠一家拆房公司,在浦东当起了拆房老板,独自干出的第一笔拆房业务就赚了30多万元。当他领取到工程款后,星夜兼程赶回了阔别数年的老家,去一一偿还30多户乡亲的欠款。不但还清了欠款,还付了5年的利息。那天,他把村里的年轻人们召集拢来:光守着土地一辈子也刨不出“金娃娃”。愿跟我到上海去挣钱的就赶快回去准备行李,每年风风光光地回来过春节。
随后,他把村里数十名年轻人带到了上海。拆房,最关键的是安全操作,在浦东的各拆房工地上经常都有民工从楼上摔下来,或是被楼上掉下的砖块、水泥构件砸伤,出了安全事故也严重影响施工队伍的声誉。黄善云自创了一套安全施工操作规程。凡新来的民工上岗前都要进行操作培训,内部实行目标管理和小承包,并签订安全协议书。各个施工队每天下班后进行安全培训,培训如何使用破碎机、剪刀机等拆房设备,每天各施工队上岗前黄善云都要带着技术人员进行技术“交底”。因此,黄善云的拆房队伍没有发生大的安全事故,在浦东很快树立起良好的形象和声誉。
1995年,随着浦东开发的加快,浦东开发区把一宗宗大的拆房业务交给了黄善云。“东方明珠”塔旁边的美食城,他仅用了一个多月就全部拆完。紧接着,浦东开发区又把陆家嘴10万平方米的动迁拆房业务交给了他。企业发展了,黄善云思考着如何提高员工的素质。他把员工们一批一批地送进技校学习。同时,不断购买新的施工机具,使自己的施工队伍成了一支能打硬仗、施工神速的队伍。
上海浦东的开发,黄善云和他带出来的民工们洒下了辛勤的汗水,在他的施工队伍里有30多名民工成了拥有百万资产的老板。坚忍不拔,吃苦耐劳的重庆民工在上海人心目中也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。而今的上海人大都知道,重庆民工为浦东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上海的市民说:“浦东一幢幢高楼,是重庆民工用身躯和汗水奠定的基石!”
我是一块“三峡石”,根在长江三峡,回故乡投资兴业是我的愿望。
“天边飘过故乡的云,有个声音向我召唤;当身边微风轻轻吹起,吹来故乡泥土的芬芳……”
这首《故乡的云》是黄善云最喜爱的歌。他说:“我虽已在上海安家,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已是上海户籍,每当我听到这首歌,都要勾起我对家乡父老的眷恋之情。长江三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,我是一块‘三峡石’,顺着长江水飘落到了上海滩,但我的根在长江三峡,回到家乡报效父老乡亲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愿望。”
黄善云在接受采访时几次动情地表达他的心迹。
黄善云告诉记者,特别是最近几年来,想家的心情更加沉重,一有空闲总爱往万州和云阳跑,到家乡会亲访友,结识党政领导,希望为家乡干点事。他曾谋划在云阳投资旅游项目,在张飞庙对岸开一家宾馆,但由于土地价格没谈好,事情只好作罢;后来又洽谈了购买三峡制药厂,又由于别人出价比他高,这项投资计划又落空了。黄善云说,在上海这十多年来,我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,总希望早晨栽树晚上就乘凉,家乡有许多项目不能马上见效益自己就退缩了。
“早晨栽树,晚上乘凉”这种思维定势是受上海的大环境影响而成。十多年来,每每承接工程时,赚钱的就干,不赚钱的不干;工程一干完,立马就结算,业主单位从不拖欠工程款。上海这地方,干部也很规矩,很少有和施工单位一起吃吃喝喝的,干事情都是来明的,很少暗地里“勾兑”。
黄善云最后对记者说,上海浦东开发已十多年,虽说还有大的商机,但我不想一辈子搞拆房工程,我随时都在思考着打造产业谋发展,在发展中打造产业。到时我会义无反顾地回报我的故乡!
三峡都市报记者 谢鸿雁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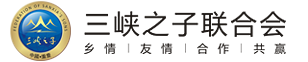
 当前位置在:
当前位置在:
